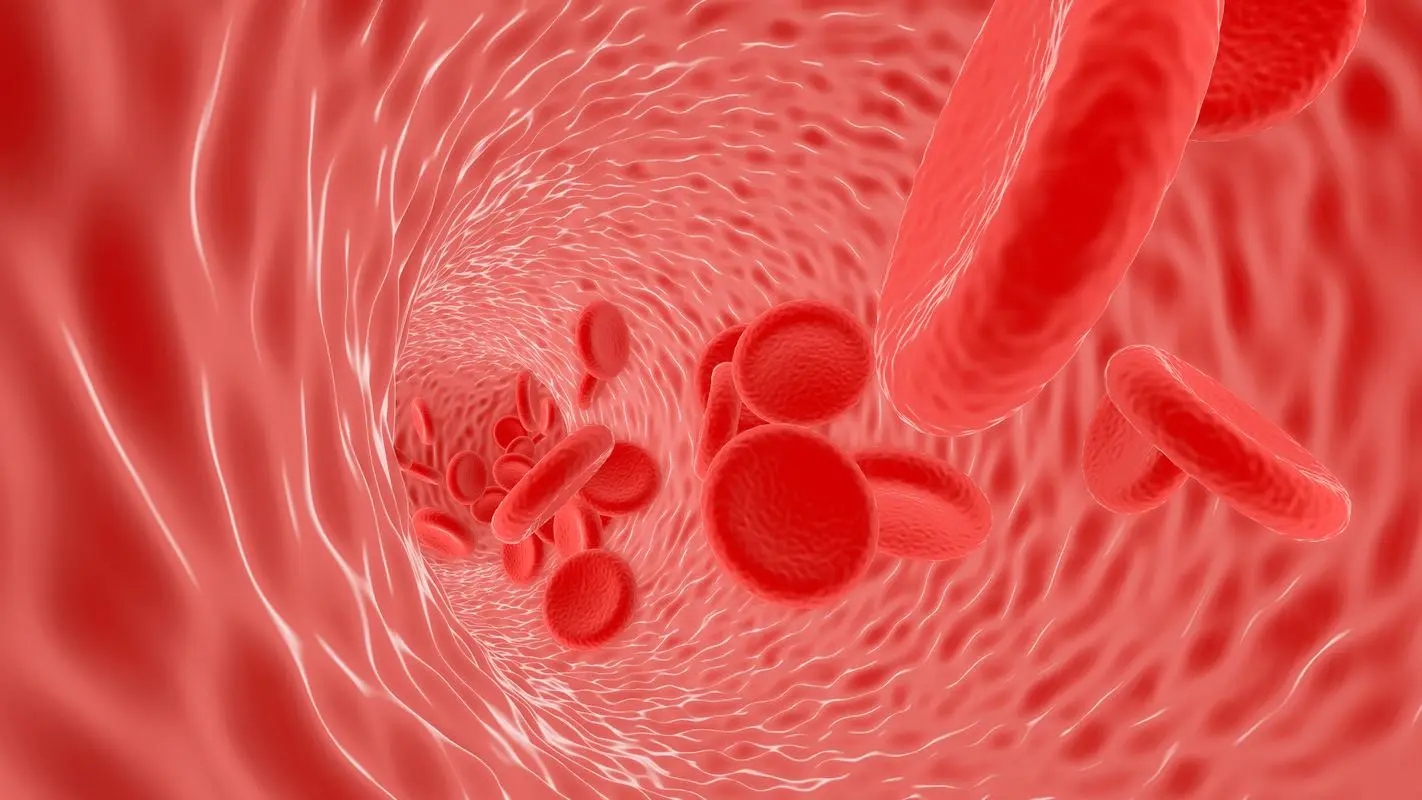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措施和其它一切安慰性、仪式性医疗活动(consolatory and ritual medication)不但是一种愚昧的医疗行为(benighted medical action),而且正在给国民经济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应当适时终止。据粗略估计,国家每年将为此支出约数百亿的医疗费用,同时,还严重影响医务人员进行其他更需要的抢救工作,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进行。承认脑死亡是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重要医学社会学问题。当一家医院的ICU里只有4台呼吸机,其中有一台被用于维持脑死亡尸体的心跳,而此时还有第五个或第六个病人等着呼吸机挽救生命时,能不能接受脑死亡这一概念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它涉及医疗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对脑死亡者的家属而言,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他们得付出大量徒劳的精力和财力,而承受同样令人悲伤的结果,所以明确脑死亡是死亡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解脱。我们也应注意到,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协助判定的6例脑死亡中,有5例均为患者家属主动提出诊断要求的。另一项调查报告表明,ICU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而在ICU抢救无效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2倍。2003年,同济医院ICU病人脑死亡后,每天的医疗费为¥3500-4000。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医疗福利资源相当有限,理应根据科学原理合理利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节省医疗资源虽然不是脑死亡立法的主要理由,也不是脑死亡立法的急切动机,但其后效显而易见。
三、 生后自爱最后的一点自我保护权,不要轻而放过
一个人既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同样也应有在死后尊严地离去的权利。“入土为安”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习惯,无论是医生还是家属都没有权利将其滞留在医院,让其遗体经受无休止的“折磨”。如果希望在脑死亡后保持遗体、遗容之尊严(VIP 公众形象等)不受愚昧医疗行为之侵害,如果希望在脑死亡后及时停止为亲人和社会增添无畏的经济和精神负担,那么接受脑死亡判定标准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同时,认同脑死亡判定可使亲属避免从徒劳的希望中遭受进一步的感情创伤。
四、 法定死亡时间精确判定的社会学意义
法定死亡时间的精确判断其社会意义在于维护医疗保险、人生保险、社会福利、财产继承、刑事责任、事故肇事方赔偿损失、家庭义务等方面的合理性。按照英国脑干死亡条例,脑干死亡判定要进行两次。其间隔时间因病情,治疗过程,病程变化而定,没有统一规定。虽然宣布死亡、停止呼吸机是在第二次确认之后进行,但法定死亡时间则以第一次判定成立时间为准。
如何准确而及时地判定脑死亡并将其作为人类死亡的判定标准是现代医学向传统医学提出的一项挑战。选择脑死亡作为人类死亡的判定标准无疑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医学科学进步的重大里程碑之一。